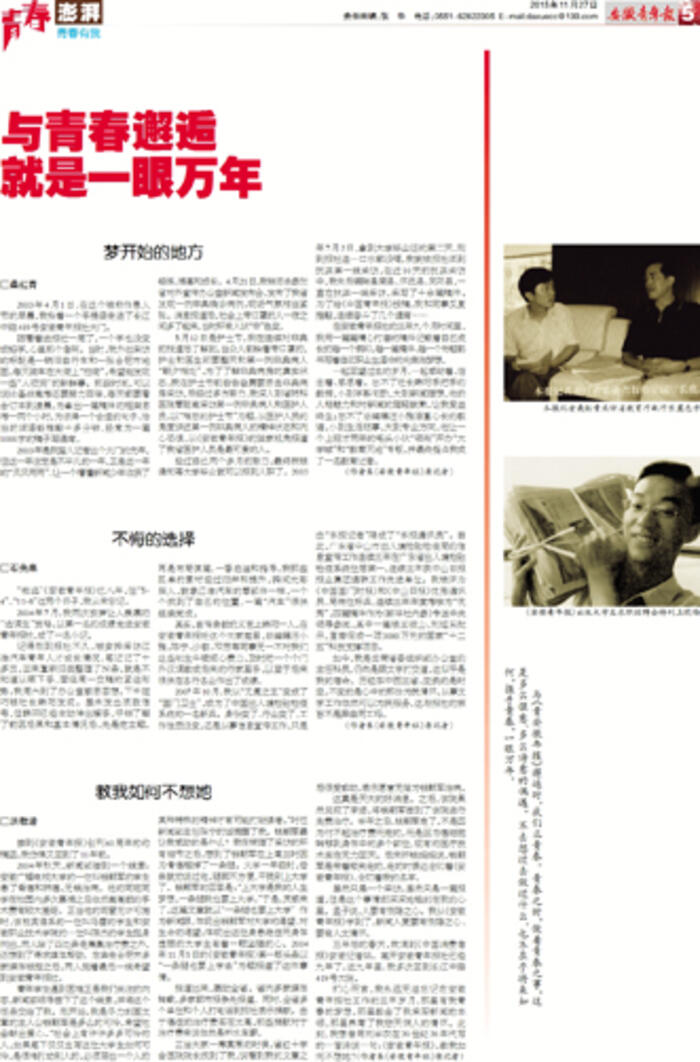梦开始的地方
□桑红青
2003年4月1日,在这个被称作愚人节的早晨,我拎着一个手提袋走进了长江中路419号安徽青年报社大门。
眼看着进报社一周了,一个字也没变成铅字,心里那个急啊。当时,我外出采访的标配是一辆旧自行车和一张合肥市地图,每天骑车在大街上“扫街”,希望能发现一些“人咬狗”的新鲜事。那段时间,可以说比备战高考还要努力百倍,每天都要看合订本到凌晨,为拿出一篇稿件的框架思考一两个小时,为求得一个合适的句子、恰当的词语能推敲十多分钟,经常为一篇1000字的稿子写通宵。
2003年是我踏入记者这个大门的元年,但这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正是这一年的“风风雨雨”,让一个懵懂新闻少年收获了锻炼、提高和成长。4月21日,我被派去参加省对外宣传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我省发现一例非典确诊病例,现场气氛相当紧张。消息报道后,社会上带口罩的人一夜之间多了起来,当时所有人谈“非”色变。
5月12日是护士节,我在连续对非典的报道后了解到,当众人都躲着带口罩的,护士和医生却要整天和第一例非典病人“朝夕相处”,为了了解非典病房的真实状态,我在护士节前自告奋勇要求去非典病房采访,后经过多方努力,我深入到省肺科医院零距离采访第一例非典病人和医护人员,以“难忘的护士节”为题,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讲述第一例非典病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恐惧,从《安徽青年报》的独家视角报道了我省医护人员是最可爱的人。
经过自己两个多月的努力,最终我被通知等大学毕业就可以报到入职了。2003年7月2日,拿到大学毕业证的第二天,刚到报社连一口水都没喝,我就被报社派到抗洪第一线采访,在近10天的抗洪采访中,我先后辗转阜南县、怀远县、凤阳县,一直在抗洪一线采访,采写了十余篇稿件。为了给《中国青年报》投稿,我和同事反复推敲,连续奋斗了几个通宵……
在安徽青年报社的三年九个月时间里,我用一篇篇精心打磨的稿件记载着自己成长的每一个脚印,每一篇稿件、每一个标题都书写着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光荣与梦想。
一起回望过去的岁月,一起感动着、惦念着、感恩着。忘不了社长韩阳手把手的教授,小到字斟句酌,大到新闻理想,他的人格魅力和对新闻的驾轻就熟,让我受益终生;忘不了总编辑汪小雅语重心长的教诲,小到生活琐事,大到专业方向,他让一个上班才两年的毛头小伙“领衔”开办“大学城”和“教育天地”专版,并最终指点我成了一名教育记者。
(作者系《安徽青年社》原记者)
不悔的选择
□石先来
“叛逃”《安徽青年报》已八年,但“5·4”、“11·8”这两个日子,我从未忘记。
2004年7月,我两次放弃让人羡慕的“选调生”资格,以第一名的成绩走进安徽青年报社,成了一名小记。
记得刚到报社不久,被安排采访江淮汽车青年人才成长情况,笔记记了十多页,回来重新归类整理了N条,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面临周一交稿的紧迫形势,我周六到了办公室敏思苦想,下午碰巧被社长韩阳发现。虽未发出求救信号,但韩阳已经主动伸出援手,仔细了解了前因后果和基本情况后,先是定主题,再是布局谋篇,一番启迪和指导,我那些孤单的素材经过归并和提升,瞬间光彩照人,就像江淮汽车的零部件一样,一个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篇“汽车”很快组装完成。
其实,言传身教的又岂止韩阳一人,在安徽青年报社这个大家庭里,总编辑汪小雅,陈宁、沙敏、邓芳等同事无一不对我们这些初生牛犊倾心费力,及时把一个个门外汉调教成后来的行家里手,以至于后来很快在各行各业作出了成绩。
2007年10月,我从“无冕之王”变成了“国门卫士”,成为了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的一名新兵。身份变了、行业变了,工作性质没变,还是从事信息宣传工作,只是由“本报记者”降成了“本报通讯员”。自此,广东省中山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信息宣传工作连续三年在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位居第一,连续三年获中山日报报业集团通联工作先进单位。我被评为《中国国门时报》和《中山日报》优秀通讯员、局岗位标兵,连续三年年度考核为“优秀”,四篇稿件作为《新华社内参》专送中央领导参阅,其中一篇被王岐山、刘延东批示,直接促成一项3000万元的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
如今,我是云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的主任科员,仍然是跟文字打交道,这似乎是我的宿命。历经东中西三省,变换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心中的那份为民情怀,从事文字工作依然可以为民服务,这与报社的宗旨不是异曲同工吗。
(作者系《安徽青年社》原记者)
教我如何不想她
□洪敬谱
接到《安徽青年报》创刊60周年的约稿函,我仿佛又回到了11年前。
2004年秋天,新闻部接到一个线索:安徽广播电视大学的一位叫钱朝军的学生患了骨癌和肺癌,无钱治病。他的同班同学在校园内多次募捐之后依然离高额的手术费有较大差距。正当他的同窗无计可施时,该校英语系的一位叫马雷的学生和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叫陈杰的学生挺身而出,两人除了四处奔走筹集治疗费之外,还想到了寻求媒体帮助。在奔走合肥市多家媒体被拒之后,两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到安徽青年报社。
青年学生遇到困难正是我们关注的内容,新闻部领导接下了这个线索,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刚开始,我是尽力刻画文章的主人公钱朝军是多么的可怜,希望社会献出爱心。“社会上有许许多多可怜的人,如果笔下仅仅去写这位大学生如何可怜,是很难打动别人的,必须写出一个人的某种特殊的精神才有可能打动读者。”时任新闻部主任陈宁的话提醒了我。钱朝军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我在梳理了采访的所有细节之后,想到了钱朝军在上高三时因为骨癌锯掉了一条腿。大学一年级时,母亲就劝说过他,腿脚不方便,干脆别上大学了。钱朝军的回答是:“上大学是我的人生梦想,一条腿我也要上大学。”于是,灵感来了,这篇文章就以“一条腿也要上大学” 作为新闻眼,体现出钱朝军对大学的渴望、对生命的渴望;体现出这位身患绝症而身体虚弱的大学生有着一颗坚强的心。2004年11月5日的《安徽青年报》第一版头条以“一条腿也要上学去”为题报道了这件事情。
报道出来,轰动全省。省内多家媒体转载,多家都市报争先报道。同时,全省多个单位和个人打电话到报社表示捐款。由于癌症的治疗费实在太高,那些捐款对于治疗费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省红十字会医院院长找到了我,说看到我的文章之后很受感动,表示愿意无偿为钱朝军治病。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之后,该院果然兑现了承诺,将钱朝军接到了该院进行免费治疗。半年之后,钱朝军走了,不是因为付不起治疗费而走的,而是因为癌细胞转移到身体中的多个部位,现有的医疗技术实在无力回天。后来听钱妈妈说,钱朝军是带着微笑走的,走的时候还念叨着《安徽青年报》、念叨着我的名字。
虽然只是一个采访,虽然只是一篇报道,但是这个事情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孟子说,人要有恻隐之心。我从《安徽青年报》学到了,新闻人更要有恻隐之心、要有人文情怀。
三年后的春天,我调到《中国消费者报》安徽记者站。离开安徽青年报社已经九年了,这九年里,我多次回到长江中路419号大院。
扪心而言,我永远无法忘记在安徽青年报社工作的三年岁月,那里有我青春的梦想,那里教会了我采写新闻的本领,那里养育了我悲天悯人的情怀。此刻,我想借用刘半农在20世纪20年代写的一首诗说一句:《安徽青年报》,教我如何不想她?(作者系《安徽青年社》原记者)

本报记者桑红青采访省教育厅副厅长虞志方

《安徽青年报》出版大学生求职招聘会特刊上现场
与《青安徽年报》邂逅时,我们正青春。青春之时,做着青春之事,这是多么惬意、多么诗意的偶遇。不去想过去做过什么,也不在乎将来如何,握手青春,一眼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