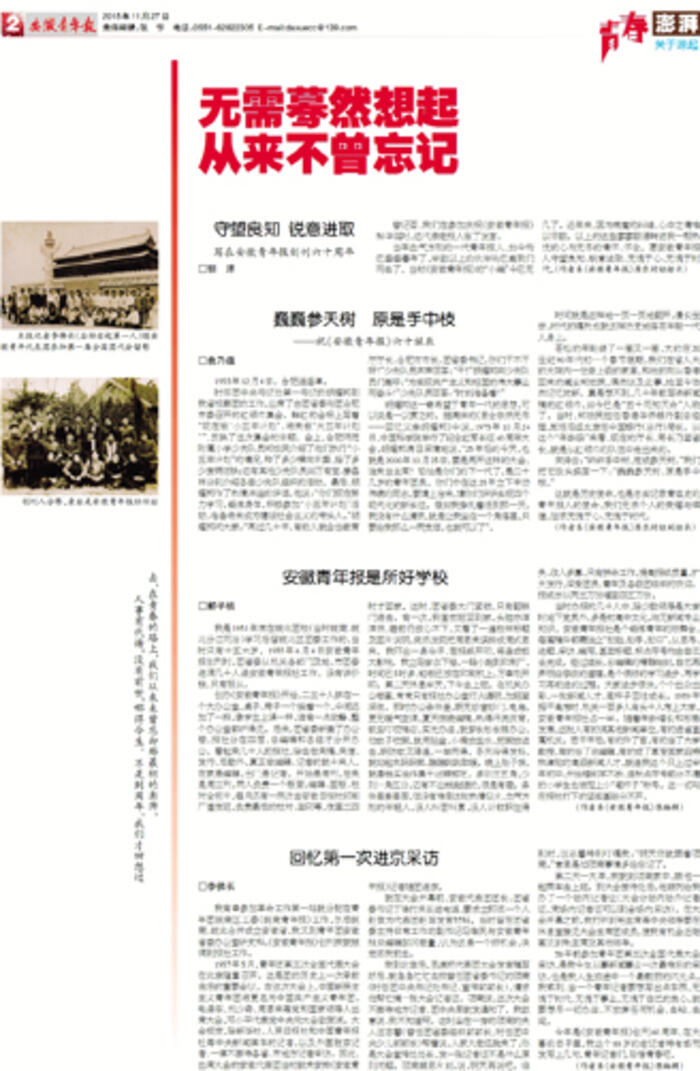守望良知 锐意进取
写在安徽青年报创刊六十周年
□胡 洋
曾记否,我们在参加庆祝《安徽青年报》50华诞时,还代表老报人做了发言。
当年血气方刚的一代青年报人,如今均已垂垂暮年了,半数以上的伙伴均已离我们而去了。当初《安徽青年报》的“小编”今已无几了。近年来,因为病魔的纠结,心中之情难以尽数。以上的这些寥寥数语转述我一颗热忱的心与无尽的情怀、怀念。愿安徽青年报人守望良知、锐意进取、无愧于心、无愧于时代。(作者系《安徽青年报》原农村组组长)
巍巍参天树 原是手中枝
——祝《安徽青年报》六十诞辰
□俞乃蕴
1955年12月4日。合肥逍遥津。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我省视察团的工作,出席了由团省委与团合肥市委召开的红领巾集会。鲜红的会标上写着“现在做‘小五年计划’,将来做‘大五年计划’”,反映了这次集会的主题。会上,合肥师范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郑效民介绍了他们执行“小五年计划”的情况,种了多少棵向日葵,拾了多少废铜烂铁;还有其他少先队员如万有宝、姜昌祥分别介绍各自少先队组织的活动。最后,胡耀邦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现在努力学习,锻炼身体,积极参加‘小五年计划’活动,准备将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带头人。”胡耀邦问大家:“再过几十年,有的人就会当教育厅厅长、合肥市市长、团省委书记,你们干不干呀?”少先队员齐声回答:“干!”胡耀邦向少先队员们高呼:“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少先队员回答:“时刻准备着!”
胡耀邦这一寄希望于青年一代的思想,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据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中说,1975年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大会,胡耀邦满目深情地说,“25年后的今天,也就是2000年10月25日,要是再开这样的大会,谁来当主席?恐怕是你们的下一代了,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团员。你们中在这25年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要请上台来,请你们讲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假如我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什么请求,就是让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也就可以了”。
时间就是这样地一页一页地翻开,漫长世册,时代的嘱托也就这样历史地落在年轻一代人身上。
苍松的年轮绕了一圈又一圈,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春节假期,我们在省人大的大院内一位老上级的家里,和他的刚从香港回来的闺女郑效民,偶然谈及此事,她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真是想不到,几十年前写进新闻稿的红领巾,如今已是“五十而知天命”人物了。当时,郑效民担任香港华侨银行副总经理,卸任后返北京任中国银行(总行)局长。从这个“年龄段”来看,现在的厅长、局长乃至省长,就是从红领巾的队伍中走出来的。
宋诗云:“纤纤手中树,定成参天树。”我们把它改头换面一下:“巍巍参天树,原是手中枝。”
这就是历史使命,也是忠实记录青运史的青年报人的使命,我们无求个人的荣耀与辉煌,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时代。
(作者系《安徽青年报》原农村组副组长)
安徽青年报是所好学校
□郭子桢
我是1951年底在皖北团校(当时皖南、皖北分江而治)学习后留皖北区团委工作的,当时只有十五六岁。1955年6月4日安徽青年报创刊时,团省委从机关各部门及地、市团委选调几十人进安徽青年报社工作。没有讲价钱,只有服从。
创办《安徽青年报》开始,二三十人挤在一个大办公室,桌子、椅子一个挨着一个,中间还加了一排,像学生上课一样,谁有一点动静,整个办公室都听得见。后来,团省委新盖了办公楼,报社分在四层,总编辑和各组才分开办公。看起来几十人的报社,除去做来稿、来信、发行、后勘外,真正做编辑、记者的就十来人,在家是编辑,出门是记者。开始是周刊,后来是周三刊,两人负责一个版面,编辑、画版、校对全包干,每月还有一两次去安徽日报社印刷厂值夜班,负责最后的校对、签印等,夜里三四时才回家。这时,团省委大门紧锁,只有翻铁门进去。有一次,我值夜班回到家,头脑亦浑浑然,睡前仍放心不下,又看了一遍校样标题及图片说明,突然发现把周恩来误排成周式恩来。我吓出一身冷汗,若报纸开印,将造成极大影响。我立马穿衣下楼,一路小跑到印刷厂,时间已5时多,铅板已放在印刷机上,万幸刚开印。第二天休息半天,下午去上班。在机关办公楼里,常常只有报社办公室灯火通明,加班至深夜。那时办公条件差,既无纱窗纱门、电扇,更无暖气空调,夏天夜晚编稿,热得汗流浃背,蚊虫叮咬难忍,实无办法,就穿长衫长裤办公,怕蚊子咬脚,就用脸盆、小桶放些水、把脚放进去,既防蚊又降温,一举两得。冬天冷得发抖,就站起来跺跺脚、蹦蹦跳跳取暖。晚上肚子饿,就凑钱买油炸臭干沾辣椒吃。多则三五角,少则一角五分,还有不出钱跑腿的,很是有趣。条件虽差虽苦,但没有难倒这批热情似火、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没人叫苦叫累,没人计较职位得失、收入多寡,只有拼命工作,提高报纸质量,扩大发行,深受团员、青年及各级团组织的欢迎。报纸亦从两三万份增至四五万份。
当时办报的几十人中,除少数领导是大学时地下党员外,多是初高中文化,均无新闻专业知识。安徽青年报社是个锻炼青年的好舞台,每篇稿件都需独立“动脑,动手,动口”,从思考、选题、采访、编写,甚至标题、标点符号均由自己去完成。经过组长、总编辑的精雕细刻,自己再弄明白修改的道理,是个很好的学习进步、再学习再前进的过程。大家进步很快,个个出众出彩,一批新闻人才、笔杆子茁壮成长。1959年招干高考时,机关一百多人有头十人考上大学,安徽青年报社占一半。随着年龄增长和形势发展,这批人有的调其他新闻单位,有的进省直属机关。若干年后,有的升了官,有的当了大学教授,有的当了总编辑,有的成了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的高级新闻人才,就连我这个只上过半年初中、开始错别字不断、连标点符号都分不清的小学生也被冠上小“笔杆子”称号。这一切与在报社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
(作者系《安徽青年报》原编辑)
回忆第一次进京采访
□李佛长
我有幸参加革命工作第一站就分配在青年团皖南区工委《皖南青年报》工作,尔后皖南、皖北合并成立安徽省,我又到青年团安徽省委办公室研究科。《安徽青年报》创刊我就被调到报社工作。
1957年5月,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团的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贺词。大会规定,除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等中央新闻媒体的记者,以及外国驻京记者,一律不接待各省、市地方记者采访。因此,出席大会的安徽代表团当初就未安排《安徽青年报》记者随团进京。
就在大会开幕前,安徽代表团团长、团省委书记丁浩打来长途电话,要求立即派一个人赴京为代表团赶写发言材料。当时留在团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马维民与安徽青年报总编辑邹冈商量,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决定派我前去。
我到北京后,迅速把代表团大会发言稿写好后,就急急忙忙去找曾任团省委书记的项南(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请求他帮忙搞一张大会记者证。项南说,这次大会不接待地方记者,团中央早就发通知了。我故意说,我不知道啊。这时坐在一旁的项南的夫人汪志馨(曾任团省委组织部部长,时任团中央少儿部部长)帮着说,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是大会宣传处处长,发一张记者证不是什么原则问题。项南凝思片刻,说,明天再说吧。临别时,汪志馨特别叮嘱我:“明天你就跟着项南。”意思是怕项南事情多给忘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项南家中,跟他一起乘车去上班。到大会接待处后,他破例给我办了一个场内记者证(大会分场内场外记者证,凭场内记者证可以到会场内采访)。在大会开幕之前,我打听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要在休息室接见大会主席团成员,使我有机会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及其他领导。
58年前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采访,是我今生从事新闻事业一次最难忘的采访,也是我人生旅途中一个最靓丽的闪光点。我感到,当一个青年记者要想写出点东西,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事业,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放弃任何机会,去钻,去闯。
今年是《安徽青年报》创刊60周年,在大喜的日子里,我这个88岁的老记者特有感而发写上几句,青年记者们,珍惜青春吧。
(作者系《安徽青年报》原编辑)

本报记者李佛长(后排右起第一人)随安徽青年代表团参加第一届全国团代会留影

创刊人合影,身后是安徽青年报社旧址
人事有代谢,没有前世,哪得今生。不是到周年,我们才回想过去,在青春的路上,我们从来未曾忘却那最初的澎湃。